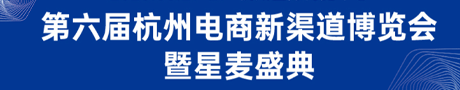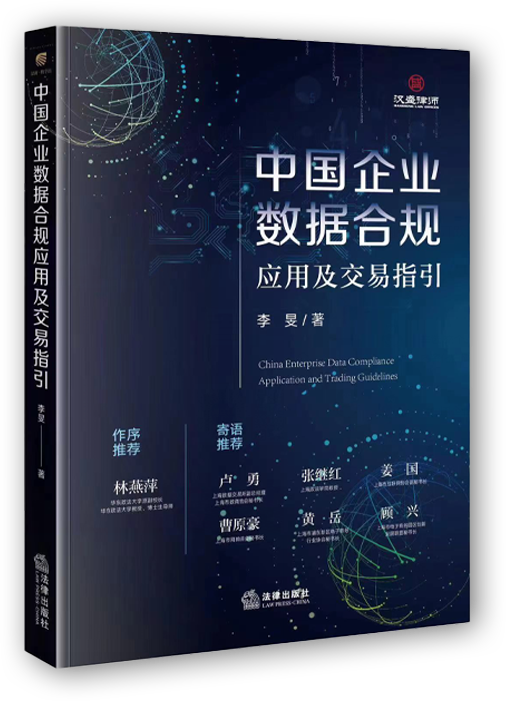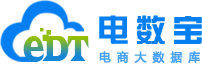(网经社讯)去年以来,国家持续加码“反内卷”,但平台经济目前仍深陷“低价竞争”、“补贴大战”泥潭亟待破解。在此背景下,数字经济新媒体&智库网经社发起——“破‘卷’立新 重塑生态” 平台经济“反内卷”调查行动(详见:https://www.100ec.cn/zt/dfnjdc/ )。这也是我们继去年“仅退款”调查行动取得重大成果后,发起更为全面、深度的调查行动,通过多维度举措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。

对此,我们组织了高校教授、协会、智库专家、投资人、律师、分析师等,对平台经济“内卷式”竞争进行深度解读,并发布了《2025年平台经济“反内卷”分析报告》(报告下载:https://www.100ec.cn/zt/dfnjdc/ )。以下为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、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学文接受 #网经社 独家专访。

网经社:当前平台经济“内卷式”竞争的形式、根源以及核心矛盾是什么?
刘学文:平台经济“内卷式”竞争的起点是价格战与补贴战。发展初期,平台依托巨额资本,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迅速抢占市场份额。当市场格局趋稳、资本支持减弱后,竞争转向更隐蔽、消耗性更强的非价格竞争,即“服务内卷”。例如外卖追求分钟级时效,电商在物流速度、“仅退款”等方面展开“军备竞赛”,这些举措在边际效益递减下,异化为平台、商户和一线劳动者之间成本与劳动强度的恶性博弈,未给生态系统带来根本价值跃升。
在此过程中,算法扮演了加速器角色:一方面,动态定价模型促使商户间展开“探底式”价格战,陷入“囚徒困境”;另一方面,强化学习算法可在无明确意思联络下,通过相互学习达成协同涨价,构成事实上的“算法共谋”。部分平台由此积累起用户、数据和资本优势,通过“平台包抄”策略跨界扩张,形成封闭的“围墙花园”,固化了市场进入壁垒。
平台“内卷式”竞争根源于其技术经济属性、资本驱动逻辑以及外部监管环境。首先,网络效应具有天然的规模扩张和市场集中趋势,易形成“赢家通吃”。加之平台服务同质化,用户黏性不强,直接导致平台为争夺用户规模展开殊死竞争,引发了前期的“烧钱大战”与后期的市场垄断。此外,作为平台运营核心的算法,既有“黑箱”特性又被赋予“隐性控制权”,能高效实施价格歧视,并为平台转嫁成本、操纵规则创造了条件。
其次,资本逻辑是关键推手。风险资本追求垄断租金的动机,驱动平台通过持久消耗战获取市场控制权,再通过提升抽成等方式攫取超额利润。即便在获得线上流量入口后,许多平台企业仍能长期维持亏损运营,其目的就是以资本优势拖垮对手。在此过程中,对商品交易总额(GMV)增速的过度追逐导致重短期增长、轻长期价值的本末倒置,将价格竞争置于技术与服务创新之上,“资本对劳动的控制”等问题凸显。
再次,制度规制存在滞后性。发展初期,政府出于鼓励创新的初衷而形成的政策支持惯性,加上监管约束不强,为“野蛮生长”提供了空间。当平台规模大到足以引发系统性风险时,监管才开始介入,而此时平台已形成“大到不能管”的局面,其市场权力、数据壁垒使有效规制异常困难。现行法律法规亦难以完全适应大数据、算法共谋、新型用工关系等新业态,常出现规则漏洞或执行困难。
网经社:这种“内卷”对平台、行业、国家造成了哪些深层次、长期的负面影响?
刘学文:这种“内卷式”竞争对平台生态、产业结构乃至国家发展产生负面影响。
首先是侵蚀平台生态,表现为价值分配失衡与信任危机。竞争转向存量后,平台为维持利润提高抽成,高额佣金、价格内卷及“仅退款”等规则,使大量中小商家陷入两难困境:要么因不加入平台而失去市场,要么在加入后因无法与巨头抗衡而利润微薄,甚至亏损。在平台用工领域,算法的精细控制导致劳动强度与薪酬不匹配,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,劳资矛盾尖锐。对消费者而言,低价实惠的背后,是选择权受限、个人数据被过度利用、隐私泄露及“大数据杀熟”等隐性成本。
其次是扭曲产业结构,抑制有效创新。宝贵的生产要素被投入同质化竞争,平台经济融资中超八成资金用于营销补贴,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足,呈现“脱实向虚”,阻碍产业升级。长期的价格战亦对全产业链造成“慢性损害”,导致产业链整体利润率走低,削弱了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力。平台“赢家通吃”的垄断逻辑抬高了市场进入壁垒,使新进入者难以为继,市场活力下降。
最后,对国家长远发展而言,这将引致发展动能不足。“内卷式”循环造成国民经济“无发展的增长”,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,并加剧社会焦虑,催生“躺平”等消极情绪。
网经社:在“反内卷”过程中,如何平衡政府监管的必要性与平台自主经营权?
刘学文:欲破除“内卷”困局,平台经济必须打破零和博弈惯性,从商业模式与法律监管两个维度系统性重塑,推动平台由“交易场”向价值共创的“创新场”转型,实现从“流量消耗型增长”向“技术驱动型价值创造”的转变。
(一)以价值创造为核心重塑平台商业模式与竞争范式
平台企业应将战略重心从追求用户与GMV规模,转向打造健康生态与提供高质量服务及内容,深耕垂直领域,并着重建立信任机制、创造差异化价值,以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,不断探索从提升用户数量(More Users)到优化匹配质量(Better Match)的创新路径。平台应建立新的内部评价体系,将考核重心转向用户满意度、商户留存率与盈利能力、技术贡献度等多维度价值指标。同时,商业模式应从向商户“抽租”,向“赋能者”转型,通过提供“软件即服务”(SaaS)、智能库存管理、供应链金融等增值服务,赋能商户降本增效,将自身模式从抽取交易佣金,转变为输出解决方案与增值服务。
在竞争策略上,应引入“竞合”思维,探索跨平台合作,摆脱价格战怪圈。更根本的突破是推动平台经济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,发挥平台数据处理、算法匹配优势,服务实体经济,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,为企业提供从需求预测、柔性生产到供应链金融的一体化解决方案。在国内市场饱和后,应积极开拓海外市场,以平台为载体带动产业生态“出海”,输出数字基础设施能力,化解国内低效内耗。
(二)平台经济治理的制度创新与监管平衡路径
面对平台经济的复杂性,政府治理必须在激励创新的同时,对市场秩序进行有效规制。
首先,在监管理念上,应借鉴欧盟《数字市场法案》(DMA)的思路,从传统事后反垄断,转向事前规制与事后监管并重,为“守门人”平台划定清晰的经营“红线”。
其次,法律工具亟待完善。《反垄断法》中需补充规制“算法共谋”的条款,如引入“可反驳的推定规则”,即当算法导致数个平台价格趋同且无合理解释时,可推定协同行为存在,以此破解“技术黑箱”的举证难题;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中需细化“反内卷条款”;《电子商务法》等法律中需引入“平台受托责任”,遏制平台滥用“技术中立”原则。此外,需加快健全覆盖平台零工经济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,界定平台用工组织者责任,并探索建立政府、平台与劳动者三方共担的社会保险新模式。
最后,有必要强化数字平台的以数据为核心的行政监管与执法机制。当前,国家数据局的核心职能在于数据战略的统筹规划与数据要素的治理,而市场监管总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网信等部门则分别在反垄断、劳动保障、网络安全等领域拥有法定执法权。关键在于构建以国家数据局为专业支撑、各执法部门分工负责、信息共享、行动一致的高效联动体系。应探索建立常态化会商与联合调查机制,形成监管合力。在此机制下,整合各方力量,吸纳算法工程师、数据科学家等组建专家委员会,为复杂案件提供技术咨询,实现对平台核心算法、数据应用的“穿透式监管”。同时,构建由政府、平台、行业协会、商户、劳动者等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,保障各方在平台核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。为平衡监管与创新,应借鉴“监管沙盒”经验,对市场创新举措给予制度包容,避免“一刀切”式监管,在规范中促进发展。
专家介绍:刘学文,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涉外法治研究中心(国家级)、中国—中亚法律查明与研究中心(国家级)、国际法研究中心(省级)研究员。兼任“一带一路”TOP10影响力社会智库“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”特约研究员,深圳高层次人才发展促进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,西安市法学会自贸区仲裁研究会常务理事,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,西安仲裁委、敦煌国际仲裁院仲裁员。
【小贴士】

本次调查行动重点关注:1)零售电商平台:包括京东、淘宝&天猫、拼多多、唯品会、抖音电商、快手电商、小红书等;2)本地生活(即时零售)平台:美团、淘宝闪购、饿了么、京东外卖、抖音本地生活等;3)跨境电商平台:亚马逊、速卖通、Temu、SHEIN、TikTok Shop、Lazada、阿里巴巴国际站、速卖通等;4)网约车平台:滴滴出行、曹操出行、T3出行、享道出行、如祺出行、哈啰出行、高德、百度地图等;5)在线酒旅平台:飞猪、携程、去哪儿、途牛、同程、艺龙等。